流动和摩擦 人才迁移外文翻译资料
2022-08-19 15:08: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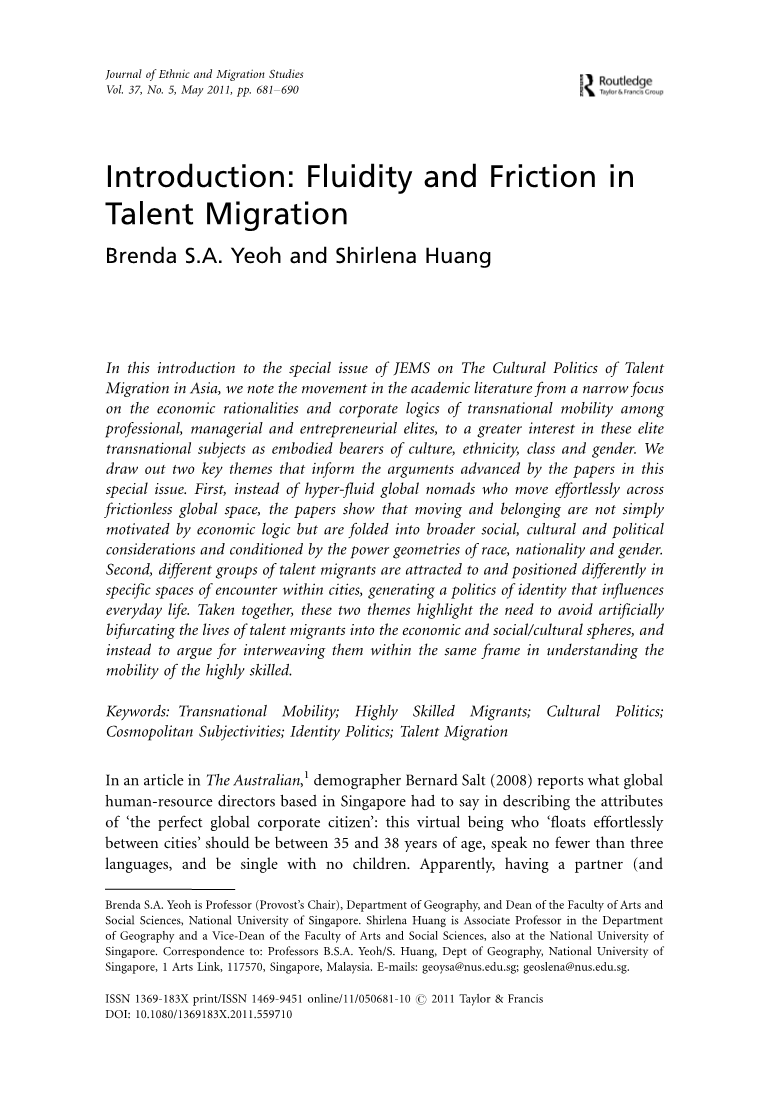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1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简介:流动和摩擦
人才迁移
Brenda SA Yeoh和Shirlena Huang
在关于“亚洲人才迁移的文化政治”的JEMS特刊的引言中,我们注意到学术文献从专业,管理和企业家精英之间的跨国流动的经济理性和公司逻辑的重点关注,到对这些精英跨国主题的浓厚兴趣是文化,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具体体现。我们提出了两个关键主题,作为本期特刊中各论文提出的论据。首先,论文表明,迁徙和归属不仅仅是受到经济逻辑的驱使,而是被纳入更广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考虑因素中,并受到种族权力几何条件的制约,而不是那些动荡不安的全球游牧民毫不费力地在不摩擦的全球空间中移动。其次,不同的人才移民群体在城市中的特定相遇空间中被吸引并定位不同,从而产生了影响日常生活的身份政治。综上所述,这两个主题突出表明,有必要避免人为地将人才移民的生活分为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而是主张在理解高技能人才流动性的同时将他们交织在一起。
关键词:跨国流动;高技能移民文化政治;世界性主体性;身份政治;人才迁移
在一篇文章中,澳大利亚的人口统计学家Bernard Salt报道,总部设在新加坡的全球人力资源主管曾在描述“完善的全球企业公民”的属性中说:这个虚拟存在的“城市之间毫不费力地漂浮”的人的年龄应在35到38岁之间,至少会讲三种语言,并且必须是单身且没有孩子。显然,有一个伴侣和被拖走的孩子构成“灾难的秘方”,因为家庭附属物需要所在城市的基础设施,如果发展不充分,有才华的企业公民的可动性(即搬迁潜力)将受到不利影响。相反,正如萨尔特(Salt)写道:“hellip;hellip;完美的全球公民必须准备向模拟婚姻的公司提供个人承诺。不需要伙伴,因为伙伴只会带来麻烦。鉴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和全球人才争夺战的爆发,早期有关专业,管理和企业家精英流动性的学术文献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也倾向于反映出这些“人才”的意识形态结构。强调这些精英跨国人员的超机动性永远在行进中,永远在过境中,永远不受限制,永远是“流动空间”的一部分,将其描绘为流动的个人职业主义者,纯粹是对公司逻辑的回应,并在公司间和公司间转移以及职业流动的激烈流动的世界中流通。然而,在最近一段时间,新兴的有关高技能经济移民的奖学金试图超越对高机动性和国际化的假设,将其描绘为文化,种族,阶级或性别的具体载体。例如,女权主义地理学家强调,有必要取消关于职业移民的男性主义假设,并研究劳动中工作中性别差异化的权力几何结构市场和工作场所,以及重男轻女的思想观念和家庭内部和生殖领域的性别权力关系,以塑造谁移动和谁留下。换一种说法,迈克尔·史密斯(Michael Smith)强调说,在不断跨越边界和进行场所活动的过程中,有必要将包括精英移民在内的跨国行为者作为跨国主体。他们不一定是新的社会主体性或世界主义理想的过犯载体,也不是那些成功地摆脱了由国家,首都或强权他人纺成的话语或物质网络的人。
新兴文献中的第二个相关举措是反驳先前的假设,即跨国精英永远是“无根商人寄居者”,“基本上对居住地漠不关心” “世界主义者”或“大都会主义者” “广阔宇宙中的居民”,他们超越了特定地方的“换文化”过程,发挥了自己的身份和归属政治,与他们所处的单个城市处于不同的阶段(即使只是暂时的)。通常,他们被描绘成不是“宇航员”,然后被描绘成没有足够“扎根”以参与本地化的“常客”,与他人共处的场所营造政治。然而,正如莱伊所论证的那样,“全球主题的广泛影响力和掌握力(指的是跨国商人和世界性专业人士),他们脱离特定群体和游击党,他们的统治地位和不受伤害的自由还很遥远。更具体地说,Yeoh和Willis认为,研究高技能的跨国移民与“接触区”建设有关的文化政治的重要性。
尽管他们具有流动性和短暂性,但国际化精英的存在确实在全球化城市中产生了许多“接触区”。并且由于他们的“存在”具有短暂和不固定的性质以及强烈的连通感与“其他地方”相比,比较长期,稳定,通常与历史根源的移民相比,这些接触区受到不同的影响,这些移民是由较长期的移民,甚至是较新的,技能低下的移民所伪造的,移民的数量更多,因此构成更强的身体感。首先,这些接触区很少出现在城市政治领域。正如Sennett所述,“新的全球精英hellip;hellip;避免了城市政治领域。它想在城市里经营而不是统治它。它构成了没有责任的权力制度。尽管可能是这样,但我们认为,国际精英的具体存在既是日常文化政治的催化剂又是媒介。”
在JEMS的特刊中,论文不再将跨国精英描绘成“知识游牧民族”,他们由于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权地位而与低技能的同行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居住在一个完全无摩擦的空间中。相反,这些贡献表明,尽管经济关系和合理性是人才流动现象的基础,但它们却被整合到更广泛的工作过程中。更具体地说,我们共同认为,必须在更广泛的文化政治中,从才华横溢的政治中才能来理解才华横溢的技术移民的举动。
迁徙与归属的文化政治
跨国精英在全球舞台上采取的行动的复杂性有点类似于在棋盘上进行战略行动的棋子,这些战略棋盘纵横交错着,有着可见和不可见的网格线和规则,有时会经过深思熟虑的思考和行动计划,有时会出乎意料地撤退,并且在两次移动之间有明显的停顿。这些举动的灵活性和暂时性反映在“移民/移徙”二元组日益明显的不足和描述这些举动所必需的不断扩展的术语上,包括“逐步移徙”,“回返移徙”,“多次移徙” ,“旅行”,“流通”和多向“(超)出行”。因此就跨国移徙进行谈判流动感的形成不仅取决于对公司逻辑或经济合理性的反应,而且还取决于在家庭-社区-国家范围内有效的社会文化-政治因素。
因此,Ley和Kobayashi强调了中国跨国公司选择的跨种族生活,在香港和温哥华之间穿梭的一系列非金钱原因,即使他们试图以更好的愿望来争夺亚洲业务。在探讨了从加拿大到中国的熟练移民的“回返移民”以及“融合与跨国主义,灵活性与根源之间,公民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张力”时, Teo说明了临时性搬家或不搬家的常见避免语是“我们将会看到;我们将再次谈论它;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因为人们选择了“不选择”。进一步的说明包括意想不到的路线,例如从北京经温哥华前往上海以避免混乱的关系,儿童教育愿望的“根基”影响,以及在没有明显成就的情况下考虑回国的“面子”问题。曾先生也以类似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台湾人出于各种原因(包括优先考虑上海的基础设施,可以支持适合国际家庭的生活方式,包括舒适的公寓,装满西餐的杂货店和各级英语学校),这违背了同质经济行为的观念。同样,何展示了新加坡移民如何对自我发展和探索的渴望可能是他们迁居伦敦的基础,即使以较低的生活水平为代价。
向将视角从个人移民的视角转变为国家视角,展示了中国政府如何不仅通过经济合理性而且通过建立充满奇观的“仪式经济”来吸引并与海外华人专业人士(OCP)互动和显示。像政治仪式一样,它具有强大的动员和合法化能力,而且正如项志强所说,在产生新的主观性之下,将OCP纳入已建立的政治秩序以及发展跨国界的新的社会和政治关系方面特别有效。经济,文化和政治都是在“礼节经济”的表现中密不可分的,尽管缝合过程中使用的螺纹却看不到。
由于“移动”是在多个生活领域中协商达成的,因此在移动之后“留下”的决定以及对各种“财产”的沉思都同样地嵌入了社会文化政治矩阵中。Teo写道,在温哥华的中国移民中,采用正式的加拿大国籍通常是一个由定居经验塑造的事实决定的,与“民族身份”有很大的区别,与其说是公民存在,不如说是公民身份对他们成长的国家的依恋感。曾则提出了不同的说法,他认为熟练的移民与“全球身份”的轻松联系是一个神话,并且“除了最高层的移民以外,大多数熟练的移民无法负担许多有效的经济和社会文化原因因而变得毫无根源”。Liu-Farrer和Ho都展示了文化资本在进入特定劳动力市场中的重要性。例如, Liu-Farrer解释说,尽管有种族和文化上的同质性,但中国留学生移民仍可以留在日本公司,主要是利用她所谓的“移民职业利基”,这取决于拥有公认的移民来自日本高等教育的教育证书,显示日语和汉语的流利程度,并且能够理解和桥接这两个社会,以协助其公司扩展跨国业务。同时,虽然职业流动和发展需要成为日本公民以显示真正的承诺,但大多数接受调查的中国移民渴望以“伪移民”的身份返回中国,主要是因为人们对“日本”的印象是为了日本人,有时是出于务实的原因,例如希望在中国抚养子女,这在学业和道德上都优于日本。
场所与认同的文化政治
在特定位置非常重视本地移动和归属的复杂性。对于跨国精英而言,这些地区通常是(尽管并非总是)全球的全球化城市,这些城市似乎在确保最大数量和质量的流动方面最成功。即使大量的跨国精英被吸引到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已建立的全球城市进行工作,但正如政府所言,在过去的两到三十年中,上海和新加坡等城市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主要交往地带,包括重建其主要城市的建筑和文化环境,不仅是为了吸引最优秀的国际人才,更是为了促进本国自身的发展。
在全球这种城市化管理和多样化的地理环境中,文化因素(尤其是在生活方式,亚文化和休闲活动方面)被认为对跨国精英,具有阶级、性别和地区血统的人们对这些城市的看法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充当了“移民目的地,成就和跨国性的关键决定性因素”。曾探讨上海如何成功吸引台湾技术移民(包括男性和女性),因为在他们的脑海中,上海已成为一种幻想城市,“如今的淘金目的地和实现现代经济目标的梦想之地”,并促进他们追求国际化的生活方式。通过关注上海迅速发展的国际风格的夜店,《花拉》还强调了上海令人兴奋的全球夜景如何吸引了众多种族和性别异类的外国人才,尤其是日本和美国。但是,不仅外国人在文化因素方面考虑地方政治。Teo和Xiang的论文清楚地表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定领域)已在特定市场(例如科学园和特别开发区)进行了市场营销,并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和计划(与物质奖励和政治仪式挂钩)以与位于北美,欧洲和澳大利亚的“海外人才”积极主动地建立新的关系,以吸引他们的“家”,潜在的回国移民会根据他们的担忧评估他们这样做的能力。例如,孩子的能力(重新)适应中国(特别是在教育方面),他们自己的能力以重新建立关系,以及亚洲的“面子”概念。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跨国主义不是“抽象的,非物质化的文化流动”的集合,而是建立在“人们生活的具体的日常变化”的基础上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每天由“移民hellip;hellip;在本国和东道国社会中”维持“多重参与”的方式。虽然“流动中的人们”的社会关系和人脉网络可能与那些不流动的人不同,但他们的日常地理位置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相当普通的。跨国关系所处的复杂性根源于移民精英在其中移动的特定跨国空间,并在其中穿越。可以说,尽管全球城市具有异质性,但全球化使跨国精英“在着陆时相对容易地hellip;hellip;通过使用已经在类似环境中获得的空间类别”。移民所在的特定跨国场所中,精英人士在全球城市中建立了社交和专业网络,其范围从工作场所到社交场所,例如海外俱乐部,外籍俱乐部,酒吧和夜总会。
即使他们在这些空间中穿行,但“大都会人物”表现出一种“愿意与他人交往”的取向。他们的根源(同族和公民)和(跨国)路线相同。许多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文揭示了在每个城市需要这些网站内的日常谈判和学习需要,在跨国精英活动所处的特定文化的机会和约束下,这些地区在种族和民族上都体现了世界主义的实践和偏见。在这些动荡的景观中,在日常工作中进行适当的操作既要了解工作场所的文化政治,也要学会学习利用社会空间发展经济关系和机会:经济和社会不可分叉。例如,何着重介绍了新加坡移民在伦敦遇到的谈判的复杂方式。她展示了新加坡人如何有选择地获得和动员文化特征和身体行为守则,是工作与社交的一部分规范,以促进他们在英国工作环境和酒吧等社交互动空间中进行“差异”和“外部性”的日常谈判。从Ho的论文以及Ye和Kelly的论文可以看出,该论文着眼于新加坡在世界主义的谈判,新加坡人的“声称的世界主义精明形式”是一个很滑的概念,在一个国际社会之间不容易被“振荡”。殖民主义时代对“白人”或“西方”优势的束手无策,一方面渴望掌握其表现,另一方面对白人的矛盾感和对新加坡渐进多元文化立场的庆祝。
在研究影响中国留学生移民在日本职业流动性的一些日常就业现实时,Liu-Farrer展示了一些中国妇女如何选择自雇以避免日本工作场所的性别文化规范(例如晋升上限),工资差异或女性同事向男性同事提供茶水的期望。Farrer对上海全球夜景的人种问题的研究揭示了这些空间中男女的特定位置:白人男性体验到“他们将民族和种族特征作为性红利的体现,一些跨国的亚洲男女也是如此,...白人女性经历了最令人痛苦的脱性形式。因此,在许多不同的跨国人才群体的日常生活中体现的流动性的模式和动态清楚地支持了这样的观念,即他们是体现在地理位置和社会地位上的社会参与者。
结论
JEMS特刊中的论文重点关注各种人才问题,不管是在职业,国籍,种族还是性别方面,即使在当前经济放缓时期,也流入和流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地区亚洲。在本系列中,从来源和目的地来看,流动的多样性人才在中国,台湾,新加坡,日本,英国和加拿大之间流动,这是对中国文化政治的话语建构和扎实实践的重要案例研究。从亚洲的角度来看,人才流动性(移动,过境,返回等)以及在跨国的相遇空间中不同人才群体之间的文化政治发挥了作用,从而允许“多点接触,结盟和冲突”。
各种案例研究还揭示了超级机动人才在“主人”和“移民”之间谈判种族和国籍的权力不对称的复杂方式。即使在所谓的国际化环境中(例如,全球城市中的工作和休闲场所),似乎也会出现预期的一系列特定于文化的行为,这些行为通常与一套种族,性别,语言和其他具体体现的规范相关联,并挑战无缝的跨国资本主义阶级的思想。返回全球人才的复杂谈判(如返回中国的移民案例))必须努力解决其身份的“分层细微差别”,因为“公民”与“国民”也对世界主义理想的普遍性提出了质疑。
最后,论文显示,运用“每天”的视角,不仅有助于揭示跨国边境对全球人才的意识形态,文化和物质影响,而且还可以清晰地描绘那些没有过日子的有才华的人。当今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但实际上他们在其“专业,社会和文化生活世界”中导航。确实,这些分析加强了侧重于“平凡地理”的有用性,以更好地揭示国际人才流动和所处的跨国工作和社会空间中运作的多种主观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411043],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