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成本的作用和清洁能源投资的去风险策略外文翻译资料
2023-03-28 11:50:18
融资成本的作用和清洁能源投资的去风险策略
原文作者 Jan Christoph Steckel,Michael Jakob
单位 波茨坦气候变化影响研究所
摘要:尽管可再生能源的成本不断下降,但在资本成本较高的国家,建设可再生能源所需的初始投资可能会构成重大挑战。在本文中,我们首先观察到,当资本成本较高时,仅碳定价不太可能足以在电力行业实现可再生能源的高份额。相反,需要采取补充措施来降低投资者的资本成本。然后,我们讨论如何通过解决投资风险的潜在来源(政策去风险)或在国内和国际层面转移私营部门投资者的风险(金融去风险)来降低融资成本。
关键词:融资成本; 可再生能源; 碳定价; 去风险
1.简介
全球能源系统,尤其是电力部门的脱碳是实现 2015 年在巴黎商定的气候目标所必需的全球碳排放减少的关键因素(IPCC,2014 年;Luderer 等人,2011 年) . 截至 2017 年 12 月,已有 182 个国家在 UNFCCC 的《巴黎协定》中承诺在 2030 年之前通过“国家自主贡献” (NDC) 减少排放。然而,这些目标并不总是得到国内政策的支持,因此对承诺的可信度提出了质疑(Nemet 等人,2017 年)。事实上,尽管排放增长率已经显着放缓与前几年相比,最近的估计表明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持续增加(Jackson 等人,2017 年)。
尽管电力部门有一系列低碳替代品,包括可再生能源(如风能或太阳能光伏)、核能和碳捕获与储存 (CCS),但许多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目前仍在扩大能源规模通过投资以排放密集型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能源基础设施来供应(Edenhofer 等人,2018 年;Shearer 等人,2017 年)。鉴于其经济寿命通常为 40 年或更长时间,这些投资会导致未来许多年的排放锁定(Davis 等人,2010 年;Davis 和 Socolow,2014 年;Bertram 等人,2015 年)。
因此,国际气候目标不仅要求工业化国家减排,而且要求发展中国家减排(Jakob 和 Steckel,2014 年)。在目前建立能源系统的国家,减排(与碳密集型发展路径的常规预测相比)的成本可能低于已经建立能源系统的国家,它们的排放基础设施的大量锁定。尽管可再生能源的成本最近大幅下降(例如,Creutzig 等人,2017年),但如果考虑到电网整合成本,它们通常比煤炭更昂贵(Hirth 等人,2015年)。很难指望贫穷国家承担这些清洁能源的额外成本。因此,正如 UNFCCC 共同但有别的责任原则所规定的,工业化国家必须承担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全部增量成本”(UNFCCC,1992年)。
为此,已经提出了几种气候融资机制。这些机制经常采用一种相当狭隘的方法,旨在逐个项目地提供财政援助。以往采用类似方法的经验,例如清洁发展机制,通常证明不会导致实际减排(Schneider 和 Kollmuss,2015 年),而且交易成本高。出于这个原因,有人建议采用更全面的视角,将气候金融置于更广泛的可持续发展背景下(Steckel等人,2017 年)。这种方法要求将碳定价作为一种效率cient 意味着减少排放,同时产生可用于促进人类发展目标的公共收入,例如扩大获得保健、教育和基本基础设施的机会。在这方面,气候融资作为碳定价的有利因素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碳定价已被确定为实现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减缓目标的核心政策(ia Edenhofer等人,2015 年; Stiglitz 和 Stern,2017 年;Cramton 等人,2017 年)。这样的价格激励了投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必要变化,并促进了实现气候稳定目标所需的技术进步(Stiglitz 和 Stern,2017 年)。全球许多国家都引入了碳定价计划,通过对碳征税或引入排放交易计划(世界银行和 Ecofys,2016); 随着中国于 2017 年 12 月启动其排放交易计划,全球约 20% 的温室气体排放被定价(世界银行和 Ecofys,2016 年)。
然而,单靠碳价格可能不足以改变能源系统和使经济脱碳。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额外的工具来解决其他市场失灵问题,作为碳定价的补充。例如,这些政策包括解决技术学习和网络外部性(Jaffe 等人,2005 年)以及资本市场上的市场失灵(Hirth 和 Steckel,2016 年)的政策)。稳定的投资环境和良好的资本获取渠道对于碳价格的有效性和变革性至关重要,特别是对于资本成本通常很高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而言。例如,东南亚、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是欧盟或美国的两倍多(Ondraczek 等人,2015 年)。预计这些国家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出现最大的能源需求增长,因此在减缓气候变化目标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如本文所述,如此高的资本成本使投资模式偏向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电力基础设施,因为与低碳能源相比,后者所需的初始投资要低得多。虽然在相当普遍的层面上得到承认,但相对较少的研究表明如何将不同的政策结合起来有效地触发低碳转型。本文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首先是由于多种投资风险导致的高资本成本可能构成碳定价有效性的主要障碍(第2 节)。然后,它提出了一些可以在国内和国际层面采用的去风险策略,以降低投资者的风险(第3节)。第 4 节总结了本文。
2. 碳价格和资本成本
碳价格对电力部门投资动态以及脱碳的影响取决于不同替代方案的成本结构。一般来说,可再生能源等低碳技术的资本密集度很高,即其生命周期成本的很大一部分需要预先融资。相比之下,对于基于化石燃料的发电技术,例如煤炭或天然气,资本密集度相当低,而燃料成本在总成本中占很大比例(Schmidt ,2014 年)。
这种成本结构的差异很重要,因为成本发生在不同的时间点。对于投资决策,未来成本(即固定运营和维护成本和可变成本)贴现为净现值,以便将它们置于可比较的基础上。每单位产出的平均贴现寿命成本通常称为“平准化能源成本”(LEC)。发电技术 i 的 LEC 可以计算为
其中 Y 是生命周期,是 y 年发生的成本,G 是年发电量(电力输出),r 是贴现率或加权资本成本 (WACC)。与前期成本低的技术相比,前期成本占比高的技术从较低的资本成本中获益更多。相反,高资本成本对资本密集型技术的伤害更大。
为了证明可再生能源投资融资成本的重要性以及碳定价对引发能源系统转型的有效性,请考虑以下典型示例。投资者面临化石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的初始投资成本和。让我们假设资本有无限长的寿命(即没有折旧)。为简单起见,假设可再生能源在其生命周期内不会产生任何进一步的成本,而化石发电承担燃料成本以及碳定价在每个时期。令 r 表示可以在市场上获得资本并因此用于贴现未来成本的利率。那么,化石发电的当前净成本可以表示为:
如果其成本的现值不超过化石发电的现值,投资者将选择可再生能源,即如果
这决定了可再生能源比化石燃料便宜的“收支平衡”利率,
在这个简化的例子中,从可再生能源即使没有碳价格也具有竞争力的盈亏平衡利率开始,将利率翻倍需要施加与燃料成本相等的碳价格(以使分子翻倍)。
在不同的国家,可以假设利率差异很大,因此,资本成本在影响技术选择方面至关重要。在一项专注于太阳能光伏 (PV) 的研究中,Ondraczek 等人。(2015)发现,对于光伏投资决策而言,资本成本的变化比太阳辐射的变化更重要。不同国家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WACC) 相差 8 倍,日本 (3.7%)、英国 (4.1%) 或荷兰 (4.3%) 等发达国家的值最低,发展中国家的值最高像巴西 (28%) 和马达加斯加 (29%) ( Ondraczek et al., 2015 )。
这些差异不仅受利率驱动,还受股权成本与债务成本、市场系统性风险和特定投资者投资组合之间的比率驱动(Brealey 等人,2011 年;Ondraczek 等人,2015 年)。资本市场准入、公司规模、投资组合以及对冲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对投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投资在哪个国家(例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哪家公司(跨国、当地、国有或私人)投资都很重要。在发展中国家,获得资本可以说更加困难,因为市场中的系统性风险(例如政治干扰的可能性)更高。
为了说明校准模型中不同 WACC 的影响,Hirth 和 Steckel(2016 年)使用批发电力市场的部分均衡模型,重点关注供应方,计算长期(绿地)最优值(EMMA ,赫斯,2013 年)。他们确定了高融资成本和高碳价格之间的明确权衡。当融资成本较低(例如,WACC lt; 3%)且碳排放定价为每吨 50 美元时,成本最优的电力组合包括 40% 的可再生能源。在相同的碳价格和 15% 的 WACC 下,成本最优组合几乎不含可再生能源。注意在使用的模型框架中Hirth and Steckel (2016)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与碳排放成反比。因此,在 WACC 为 15% 时,碳定价高达每吨 50 美元时没有显着的减排效果,但在 3% WACC 和相同的碳价格下,排放量将减少约 40%。
这种关系如图1所示(Hirth 和 Steckel,2016),它描述了 WACC 和碳价格的可能组合,以在电力组合中实现一定份额的可再生能源(由等高线图中的相应数字表示)。显然,所有线都是向上倾斜的,这表明更高的 WACC 对应于更高的碳价格,以达到给定的可再生能源份额。然而,更有趣的是,随着可再生能源份额的增加,轮廓变得更加陡峭。也就是说,对于更雄心勃勃的气候变化减缓目标,增加 WACC 会导致所需碳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对于 10% 的可再生能源份额,将 WACC 从 5% 提高到 10% 会使所需的碳价格从大约 20 美元增加到 35 美元。相比之下,对于 30% 的可再生能源份额,WACC 的相同增长将提高碳价格从大约 45 美元到 45 美元大约100美元。
在查看由此产生的发电组合时,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动态。在根据中国(山东省)负荷数据和可再生能源基本面校准的模型应用中,图 2 (改编自Hirth 和 Steckel,2016 年)展示了能源系统如何在特定范围的 WACC 下对碳价格做出反应。在 WACC 非常低的情况下,风能、太阳能和 CCS 将占电力组合的 60%,碳价格为每吨 CO 2 50 美元。然而,当 WACC 高于 7% 时,不会发生投资变化和由此产生的脱碳。即使在每吨 CO 2 100 美元的高碳价格下,25% 的非常高的 WACC 也会阻止能源系统转型。请注意,当包括天然气(未显示)时,情况不会发生质的变化,但天然气会以非常高的 WACC 取代煤炭(Hirth 和 Steckel,2016 年)。也就是说,在 WACC 等于或高于 15% 的情况下,天然气将取代图 2中的煤炭. 然而,在目前投资煤炭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天然气通常不可用(或需要大量基础设施投资)。
3.降低投资风险的政策选择
正如上一节所讨论的,高昂的资本成本将严重限制碳价格的有效性。高资本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市场和技术风险带来的投资风险(Torvanger et al., 2016 )。如果投资者不确定某个项目是否会在长期内产生预期回报,他们只会在获得适当的风险溢价时进行投资,这会增加资本成本。出于这个原因,降低政策不确定性(政策去风险)或将风险从私营部门投资者转移(金融去风险)的措施可以降低资本成本,从而提高碳价格的有效性。
投资风险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最为明显,这些市场经常遭受制度薄弱(例如,由于缺乏监管和行政能力以及腐败)以及清洁能源市场通常不成熟的影响。出于这个原因,本节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降低这些国家清洁能源投资风险的选择上。表 1概述了将在下面详细讨论的问题。
3.1.政策去风险
大量文献强调可信度对于长期政策设计的重要性(Hovi 等人,2009 年;Brunner 等人,2012 年;Helm 等人,2003 年)。在这种情况下,可信度可以理解为期望现有气候政策将保持不变,并根据需要得到加强,以实现政府宣布的目标(Nemet 等人,2017 年)。该文献标识政策制定者可能偏离已宣布目标的众多原因(例如时间不一致或政治利益集团格局的变化)。私人投资者的政策引发的风险还包括建设延误、征用以及预期付款的主权违约(施密特,2014 年)。
Nemet等人基于货币、财政和贸易政策的经验教训。(2017 年)开发了一种政策设计特征类型学,这些特征对于制定可信的气候政策至关重要。根据本小节所建立的框架,可以通过灵活的规则设计、提高透明度、解决分配冲突以及稳健的政策实施来减少政策不确定性。因此,这些措施可以被视为降低投资成本的最佳政策,因为它们旨在消除投资风险的潜在来源。
3.1.1.灵活的规则
法律和法规的设计需要确保经济主体期望它们保持不变。然而,与此同时,他们需要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不可预见的事件(Brunner et al., 2012 )。这种灵活性和承诺之间的权衡可以通过允许根据如何考虑新信息(例如关于气候影响或缓解成本)的预定处方修改给定目标来进行导航(Jakob和 Brunner,2014 年)。
通过允许“安全阀”来指定在哪些条件下可以放松现有气候政策,可以实现更可信的政策。例如,排放交易计划可以包含一个最高价格阈值,超过该阈值的额外许可将被注入市场,直到其价格恢复到阈值。尽管这样的结果可能导致无法实现已宣布的气候目标,但它仍然比出于政治原因放弃气候政策的情况更为可取,例如防止能源密集型行业过度失业。由于它们降低了政策逆转的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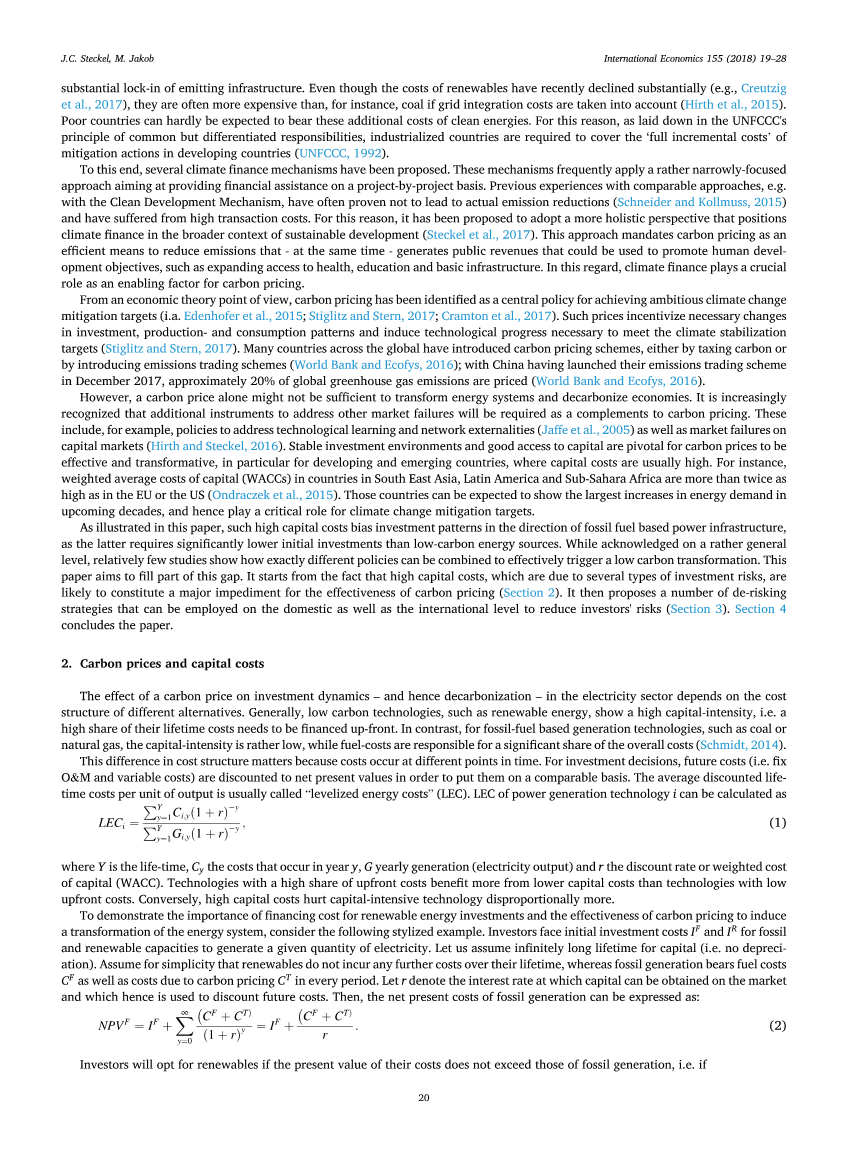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0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597796],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