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男孩还是女孩?”重新思考凯迪克奖获奖绘本中的性别角色表征,1938-2011外文翻译资料
2022-08-26 16:26: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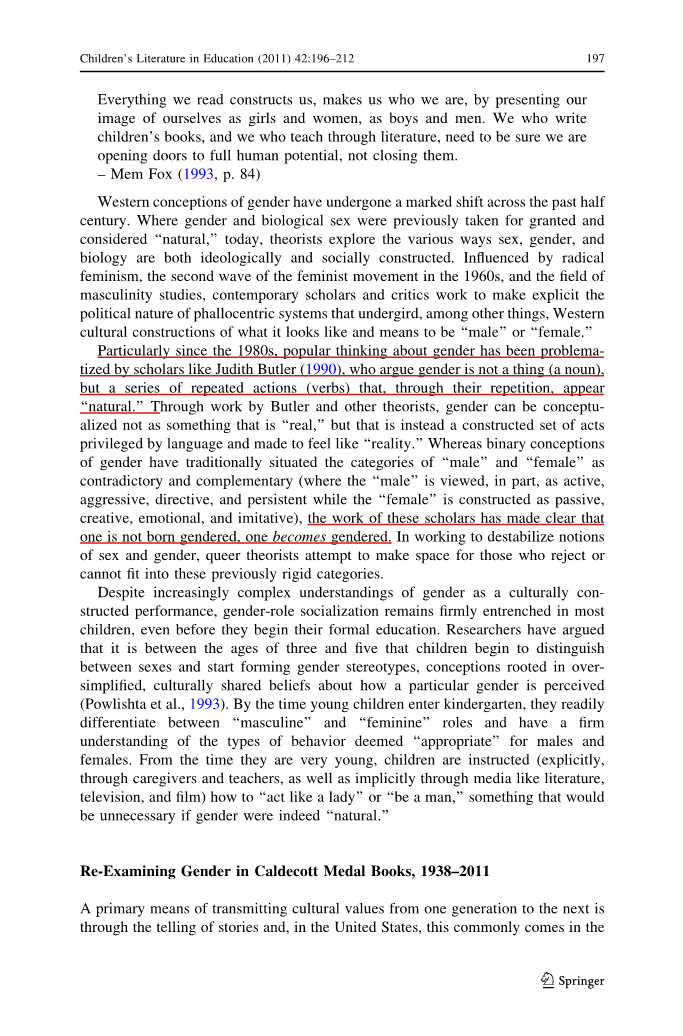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17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这是男孩还是女孩?”重新思考凯迪克奖获奖绘本中的性别角色表征,1938-2011
托马斯bull;克里斯普bull;布列塔尼bull;希勒
发表于 2011 年 3 月 15 日 斯普林格科学 商业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11
以往的许多研究都在凯迪克奖获奖绘本中探讨了性别角色定型问题。基于对凯迪克书籍中女性表现形式的广泛研究,本研究通过探索“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生物性别和性别在这些文本中的构建方式,提供了一个关于1938 年至 2011年凯迪克奖章获奖文学中性别是如何表现的批判性调查。创作者们在脱离以前的学术研究之前,简要地讨论了作者和插画家的性别以及男性和女性在图画和文本中作为人物或形象的表现,以便重读以“无性别区分的”主要人物为特征的书籍,这些书籍在文本中没有被确定为”、“男性”或“女性”,因此可以根据个别读者的解释。通过抵制性别和生物性别的文化暗示和规范性建设,这些无性别区分的描述扩大 了读者可能以各种方式看待他们自己或他们生活中的那些人的范围。
关键词 凯迪克奖;获奖;绘本;性别
我们阅读的一切构造了我们,塑造了我们,通过展现我们作为女孩和女人的形象,作为男孩和男人的形象。我们写儿童书籍,我们通过文学进行教学,我们需要确保我们是在开启人类全部潜能的大门,而不是关闭它们。-MemFox(1993,第84页)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西方的性别观念发生了显著的转变。性别和生物性别以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并被认为是“自然的”,今天,理论家们探索了性、性别 和生物学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建构上的各种方式。受到基进女性主义、20世纪6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以及男性气质研究领域的影响,当代学者和批评 家们致力于明确支撑西方文化建设的男性中心系统的政治本质,这些文化建设包括它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和意味着什么是“男性”或“女性”。
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行的性别思维已经被朱迪思·巴特勒 (JudithButler,)等学者问题化,他们认为性别不是一个东西(名词),而是一系列重复的动作(动词),通过它们的重复,显得“自然”通过巴特勒和其他理论家的研究,性别不能被概念化为“真实”的东西,而是被语言赋予特权并让人感觉像“真实”的一系列行为传统上,性别的二元概念将“男性”和“女性”两类视为矛盾和互补的(在这两类概念中,“男性”部分地被视为积极的、进攻性的、指令性的和持久的,而”女性”则被构建为消极的、创造性的、情感的和模仿性的),但这些学者的工作已经表明,一个人不是生来就有性别的。在致力于颠覆性别观念的过程中,酷儿理论家试图为那些拒绝接受或不能适应这些先前僵化的类别的人们创造空间。
尽管对性别作为一种受文化制约的表现的理解日益复杂,但性别角色社会化在大多数儿童中仍然根深蒂固,甚至在他们开始正规教育之前。研究人员认为,儿童在3岁至5岁之间开始区分性别,并开始形成性别陈规定型观念,这种观念植根于对特定性别如何被感知的过于简化的文化共同信念(powlihta 等人)。当幼儿进入幼儿园时,他们很容易区分“男性”和“女性”角色,并对被认为“适合”男性和女性的行为类型有着坚定的理解。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他们就被教导(明确地,通过看护人和老师,以及通过文学、电视和电影等媒体)如何“表现得像个淑女”或“成为一个男人”,如果性别确实是“自然的”,这些都是不必要的。
重新审视凯迪科特奖章图书中的性别,1938-2011 年
将文化价值从一代传递到下一代的主要方式是讲故事,在美国,这通常来自于儿童文学的形式。儿童文学中的信息不仅为理解世界提供了模型,也为理解自我提供了模型,因此儿童文学中的信息有可能深刻地影响年轻读者的生活。在这些书中,对“女性”和“男性”或“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的无处不在的描述往往是不容置疑的。毫无疑问,儿童文学中描绘的人物塑造了儿童对社会认可的角色和价值观的概念,并表明了男性和女性应该如何行 动”(Korenhaus 和 Demarest,1993 年,第 220 页)。这些关于生物性和性别的隐含信息构成了什么是“正常”或“自然”,什么需要批判性地审问(Walkerdine, 1990),因为 那些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观往往是读者必须最密切关注的(Rosenblatt,1995/1983)。
为了研究电视图书中的性别分布和性别行为结构,许多研究都集中在凯迪克奖获奖图书上[1]。以 19 世纪插画家 Randolph Caldecott的名字命名的凯迪克奖章,每年由美国图书馆协会授予“美国出版商在前一年以英文出版的最杰出的美国儿童图画书艺术家”(儿童图书馆服务协会[ALSC],第 10 页)。作为最负盛名的儿童图书奖,凯迪克奖章保证了获奖图书的惊人销量:凯迪克奖章和荣誉图书的订单几乎遍布全国的每一所学校和公共图书馆。因为图书管理员、教师和看护人员没有时间阅读任何一年里为儿童出版的每一本图画书,他们经常依靠奖励来帮助他 们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图书收藏(Brown,2008/1958)[2]。正如Beverly Lyon Clark(1992)解释的那样,“任何一个有自尊的美国图书馆,只要是为儿童服务的,那么无论它的预算多么紧张,都一定会在那一年获得奖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学者和评论家们经常关注凯迪克的书。获奖的图画书,像那些获得凯迪克奖章的图画书一样,“需要根据谁的知识被认为是最好的,谁的生活在这些图画书中得到体现来审查”(Albers,1996,第 269 页)。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建立在以前的学者完成的工作,通过检查每个凯迪克奖章的获奖者从开始到 2011 年,在这一年,这篇文章是写。先前凯迪克研究的一些作者着眼于几十年来的获奖作品(Nilges和Spencer,2002;Clark等人,2003),而 先前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研究奖章和/或荣誉书籍(Nilsen,1971,1978;Engel,1981 ;Kolbe and LaVoie,1981;Dougherty和Engel,1978;Williams等,1987;Albers,1996),有时还包括 凯迪克奖获奖者之外的文学作品,比如 Newbery 或科 丽塔·斯科特·金获奖者或 金色童年系列童书(Weitzman等人,1972;Clark等人,1993;Hamilton等人,2006)。在本文中,我们 仅仅探讨了凯迪克奖章获得者的作品,这是由于空间的限制和以往的研究表明,获得凯迪克奖章的绘本图书一般代表了荣誉图书的内容以及已出版儿童 文学的大部分内容(Korenhaus 和 Demarest,1993)[3]。
通过查阅凯迪克之前的研究,我们可以立即清楚地发现,研究人员通常依靠插图中的视觉描述来确定一个角色是“男性”还是“女性”(即“这个角色看起来 像男人还是女人?”[4])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澄清性别差异,也会参考文本(Nilsen,1971;Williams等人,1987;Clark等人,1993;Albers,1996),并且至少有一次,那些被描述但没有被确定 为男性或女性的人物“按照名字、身体特征、服装或人称代词”被标记为“中性”(Engel,1981,p.647)。在本研究中,这些先前的研究结果是有问题的:依靠插图中的视觉线索来确定一个人物或数字的性别,必然需要依靠规范性结构或个人对其含义和外表的理解(即假设携带钱包或穿裙子表明一个人物是女性或穿 西装的人物是男性)。它优先考虑这些性别可能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出现的特定概念:在“现实”世界中,有自我认同的男性怀孕和/或穿裙子,有自我认同的女性留着胡子和胡须和/或穿着燕尾服。如果一本书的文本中没有明确区分性别,那么读者最终就要解释所描述的人物的性别身份。[5]
在某些情况下,以前的研究人员决定根据孩子可能遇到、参与或解释特定 图像的方式来对图像进行分类(例如,Engel,1981;Albers,1996)。例如,汉密尔顿等人(2006) 写道:“如果我们相信孩子们可能将一个字符解释为男性,我们将其编码为男性”(第 761 页)。这种立场也有一些困难,因为它依赖于一个成年人对于所有孩子如何思考和看待世界的信念。由于儿童对文学作品的反应和成年人一样多种多样,这种一般性的假设(就像其他关于“所有儿童”的假设一样)经不起推敲。假设成年人可以决定儿童可能对某一文本作出何种反应,往往限制了可能的解释范围;这种假设依赖于关于儿童性质的文化假设和一种构建的文化假设一个虚构的“孩子”的视角它假定儿童对世界的理解不包括那些不符合性别规 范结构的人(实际上,他们可能是看护人、亲戚、朋友等)。此外,这些分类限制了提供给读者的可用主体。他们没有为那些不符合(或者拒绝)“男性”或“女性”二元分类的人腾出空间,那些可能,作为两个例子,自我认同为酷儿或变性人的人。在这个项目中,我们不关心试图想象“大多数”儿童将如何看待这些图像,也不试图猜测插画家打算如何解释图像的读者。相反,其目的是在凯迪克奖获奖图画书中找到可能存在的空间:在这些空间中,个别读者可以看到自己的镜子或生活中人物的图像。
关于凯迪克奖的一个流行的误解是,它只是一个插图奖。事实上,该奖章将年度“最杰出的图画书”作为一个整体予以表彰,该图画书的插图画家将获此殊荣。图画书体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定义既取决于内容,也取决于格式,插图通过反映、延伸和/或与文本矛盾,在意义的建构中发挥着与文字同样大的作用(如果不是更大的话)。正如佩里·诺德曼(Perry Nodelman,1988)所指出的,虽然通过语言(或者通过观看图片后可视化的“故事”)所引用的图像几乎是无限的,但图画书中的文字和图片并不是“像任何一种图画本身那样具有开放性”,这导致了一种互动和独特的交流节奏——文字和图片之间的交替— —读者既可以单独参与(图片或文字),也可以相互交谈(图片和文字)(第七页)。因此,在确定这套书中的性别表征时,我们依靠词语,通过诸如代词(即他或她)、标题(即先生或女士)或性别特定语言(即兄弟或姐妹)等文本特性,将特定字符明确地区分为“男性”或“女性”。如果文本中没有明确指出一个角色是“男性”还是“女性”,这些数字就被归类为“无性别区分的”
克拉克等人(2003 年)研究凯迪克的书籍的情况下,将出版的文本在置于他们产生的文化环境中。这项工作是有价值的,因为它对于探索文学在其创造和发布的文化背景中是重要的(Crisp,2009):书不存在于真空(Rosenblatt,1995/1938),像所有文学,图画书流派在感知的文化规范中受影响的变化(Lewis,2001)。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没有忽视语境在呈现给读者的结构中所起的作用,而是探索了这些书可能对当代读者说话的方式,一种重读或“回顾”旧文本的方式,这种方式被称为“修订”(Rich,1972),以及对主要信息和解释的“抵制”(Fetterley,1978)。本研究以凯迪克奖获奖绘本中的性别对话为主线,重新审视了以往的研究可能以性别化的方式对人物进行分类,而不是将这些人物分类为“无性别化” 的表征。
在整合这项研究的工具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之前研究人员完成的工作,并试图复制他们的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我们收集了作者和插画家的性别数据,单性别插图(只描绘女性或只描绘男性的插图)中男性和女性角色(人类和非人类)的数量,以及每本书中描绘的男性/女性/非性别角色和数字的数量。除了这些计数,我们使用了艾伯特 j 戴维斯(1984 年)建立行为定义,查看在每本书中多达四个主要人物的描述方式。
在完成完整的研究之前,我们使用研究工具独立分析从过去20年(1991- 2010)凯迪克奖获奖文献。然后我们比较我们的结果,看看我们的标签和分类是如何紧密地一致。我们发现,我们的个人计数之间的差异,图像中的数字总数,以及行为属性分配给主角。通过讨论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觉得一个角色符合某个特定的属性(例如,这个角色在哪些方面是合作的?),我们决定是否一个特定的阅读方式是由文本保证,或如果某个特点是开放的解释。
在试点完成后,我们得出结论,在进行全面研究的最佳方式是在比较结果之前独立阅读和分析这些书籍。换句话说,当我们坐在一起时,我们阅读每本书并独立完成分析,然后立即比较我们的发现。遇到相互冲突的数字或数据时,我们会一页一页地移动文本,一起工作,直到达成共识。彼此密切合作还使我们能够通过要求彼此澄清观点来检查我们自己的假设和误解(例如,问一些简单的问题,例如,“文本中哪里说这个角色是女性”或者“你怎么知道那是个男人?”)。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取得了一些发现,这些发现可能是我们在单独工作时遗漏的。举个例子,有时候我们中的一个人有一本书的精装本,但是另一个人有一个没有精装本的版本(例如,一个平装本)。通过检查这些不同的版本,我们发现虚体元素有时能够识别出一个字符的性别,而这个性别在整个文本中都没有被区分。因此,我们决定不考虑这些类型的腹面特征所揭示的信息,因为这些元素在本书的各个版本中并不一致。
通过描述计数而计数:作者,插图画家,男性和女性代表方面的一般发现
在着手考虑凯迪克奖获奖绘本中没有性别区分的角色的具体表现形式之前,更广泛地查看有关凯迪克奖获奖作家、插图画家以及男性和女性角色/人物的统计数据是有帮助的。在74个获奖作品中,共有79个作者(有些是团队合作的)。利用传记和出版商信息,我们得出结论,凯迪克奖获奖图书的作者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412018],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