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群体话语的自叙事: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性外文翻译资料
2023-01-01 19:07:59
作为群体话语的自叙事:王安忆小说中的女性主体性[1]
Bonnie S. McDougall
苏格兰中国研究中心
爱丁堡大学
I
现代小说作为主观表达手段的可能性已在本世纪由许多中国作家探讨过。受西方和日本模式的启发,许多现代中国最知名的作家选择了小说(而不是诗歌或散文,因为他们可能更传统上已经这样做)来反思他们的情绪和态度。任何手中的主观小说都可能是自传性的。中国现代作家描绘的内心世界选择作为他们的主角(通常是他们的叙述者),他们的社会身份和经历与他们自己的身份接近或难以区分,这并不奇怪。
即使在最压制性的文学控制时期(如1966-76),小说作家也可以使用相当广泛的叙事风格:例如,使用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的声音,叙述与对话之间的区别,无所不知或单一的观点,以及可靠或不可靠的叙述角色?这些设备一般都很受国内外观众的好评.西方评论家指出,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初是从西方进口的,他们有时声称他们比国内读者更了解作家的选择以及他们对他们的看法。人们并不总是能够理解的是,本世纪许多中国文学作品所引用的“自我”不一定是个人的“自我”,而是作为他们所属的特定社会群体成员的“自我” 。
本文通过对比上海当代作家王安忆的两部作品,以及鲁迅,郁达夫,丁玲,郝然和写作夫妇王喆成,温晓宇等其他男女作家的简要借鉴,对现象进行了审视。首先,我想澄清论证中的一些关键术语和概念。[2]
自主、自我,群体意识与社会秩序
西方自治个体自我的抽象极性与亚洲以群体为中心的自我相对立,主要是西方文化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创造。尽管通过对西方和亚洲政治家的认可而广泛流通,但这些结构在两端都受到人类学家在过去二十年中的不断修改,特别是对于亚洲和西方社会中可能表明历史的变化而不是地理类别。近代中国和日本的作家在西方的语言和文学借用也倾向于以最明确,最极端的形式模糊这两种结构之间的差异。
但是,从简单的极性撤退有其自身伴随的危险,然而,在另一种文化沙文主义中,假定类似的表达具有类似的指示。在中国案例中,从西方来源借用(或重新发明)的术语,通常对原始语境知之甚少,对土着文化传统理解甚少,这在新的语境中可能意味着任何事情或没有意义。只要参与者在任何特定话语中具有大致相同的背景,那么中文[3]中的“个人”,“自我”,“文学”和“知识分子”等词语的语义历史可能并不重要,特别是在新的语境中。然而,在跨文化交流中,这些差异造成的混乱可能是深刻的。
现代西方汉学中最顽固的领域之一就是关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社会秩序中的地位。与东欧国家和苏联国家相比,大致相同的时期,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末的中国历史表明,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持续的相互支持,而前者显然缺乏这种支持。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正在研究中国作家所属的社会群体(知识分子)与“自我”之间的关系(就像它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的那样),并且通过牵连,考察该群体之间的关系到社会秩序。就连王安忆的小说所表达的女性主体性也比性别认同更多地归因于社会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的定义
本文中的“现代中国文学”指的是由本世纪初至今的中国出生和成长于大陆的作者创作的书面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的集体,通常但不一定一种自觉的现代模式。就本条而言,该术语不包括以养育和主要居籍在香港,台湾或海外侨胞中心的作者撰写。暗示对被排除的材料没有价值判断。
通过将这个术语限定为书面文学产品,我遵循现代中国文学术语文学中隐含的信息,以及习惯的家庭用法。 “文学”这个词可以被称为“文化学习”,指的是需要学习的书面文本:那些通过持续研究获得书面文化的人所生产和消费的商品。
现代中国作家的身份
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现代作家的传记信息使我们能够勾勒出一位典型作家(文学家,或“扫盲学习专业人士”)的有用资料。[4]简单地说,我们可以观察到他/她来自受过教育的家庭,并且她/她自己接受过高等教育(尽管偶尔没有通常机构的好处)。除少数例外,这些作家主要将自己标识为知识分子。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一词的使用范围比西方更广泛和更狭窄。从最广泛的层面来说,它可以指所有接受过高等教育以上学历并且从事需要识字能力的职业的人。令人困惑的是,在州和党的官僚体系中有资格和受雇的人有时会被归类为知识分子,或者有时不会分类(例如,在主流政治家认为“知识分子”被敌视社会和政治发展的时期)。正如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己常用的那样,“知识分子”一词是指受过教育的人,不包括政治家和官僚。 (在这方面,毛泽东的地位尤其明显含糊不清)。再说一遍,更令人困惑的是,“知识分子”一词通常也用于更有限的意义上,指的是“高等知识分子”知名作家,记者和学者。
尽管“知识分子”这个术语可以被理解为“具有知识的社会中的元素”,但上面提到的最后一种用法表明,高度的识字能力通常表现为文学的掌握,是知识分子的决定性特征。中国扫盲,文学和社会政治力量之间的古代联系,1905年打破了官方考试制度,并没有被现代知识分子所遗忘。现代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通向政治权力的自动路径,但仍保留对识字率的垄断,因此制定了一项新的战略,以确立其在社会秩序中的社会和道德领导权。对文学的控制,文学,是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却造成了一个尴尬的冲突:在作家声称代表全国发言的同时,他们的工作仅向全国观众的一小部分提出。[5]因此,现代中国文字的一个普遍特征是:马斯顿安德森将其视为一种现实主义虚构中的“道德污点”的印记[6],或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称为“扫盲的焦虑”。
中国现代作家几乎总是认同自己,而且通常被别人认为是“知识分子”,这表明一系列特征不一定与现代西方社会中的“作家”形象有关 - 特别是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7]作为知识分子,中国作家对他们的命运有相同的信念,认为他们是国家的合法社会和道德领袖,在现代中国,这个角色普遍受到挑战,篡改,破坏或忽视,他们的工作形成了需要重申或捍卫他们认为是他们的命运的角色。
中国现代文学的推定观众
尽管中国现代国家的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性质以及该国官方声称,但似乎没有理由假设中国存在单一的观众。然而,它所获得的普遍接受的神话导致了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阅读受众缺乏详细研究。因此,以下图式是名义上的,主要基于印象派的轶事证据。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读者似乎是中国大陆的城镇知识青年,在老年人,更强大,更有才华或更有争议的作品的情况下,他们的长辈会大量涌现,诸如毛泽东,鲁迅或北岛。读者调查确实存在倾向于专注于这个观众。城市上班族,特别是在官僚机构的教育和文化部门,也可以加入这个群体。
次级读者包括“文学知识分子”(对其他作家,编辑,评论家和学者等文学专业感兴趣的读者),特别是1942年以后,负责文化事务的政治和官僚人员。大多数作者在写作时至少要注意观众,因为这些观众决定他们的作品是否会发表,以及他们的作品在何种程度上将被视为成功。
中国现代文学也有越来越多的有影响力的第三听众:中国以外的读者,包括西方的汉学家和其他学者以及学术和文学的海外华人读者。虽然他们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读者与中国作家的知识分子有很多共同点,并且倾向于与他们密切联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学生和现代中国文学学者的这种倾向增强了,因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表面接触变得很普遍。第三位观众很少挑战第二位观众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与第二位观众合作,保持第一位观众早已失去兴趣的活着作品。
这三位读者的读者总数可能是巨大的,但仍远远低于中国总人口,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农村人口大部分是“现代中国文学”的读者,正如上面所定义的那样[8]--除了为了政治目的而分配阅读的特殊情况,例如毛泽东的诗歌。大多数第二和第三位观众有兴趣在公众面前保存它选定或确定为正典的文献。
所有这些读者都可以与第四位读者区分开来:中国以外的国家的人们为了享乐而读书,选择来自任何年龄或任何国家的书籍,可能是通过时尚或宣传推动的,但没有别有用心的塑造他们的反应。 (例如,我想到的是拉丁美洲小说的非专业读者。)近年来,北美,西欧和澳大拉西亚的普通读者对近代中国的态度很乐观。尽管如此,第二和第三位观众所推广的产品并没有得到第四位观众的热烈响应,尽管这些读者的善意基金显然是无底的,但中国现代文学的翻译似乎最终仍然是余下的。
最近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前三名观众对阿成小说的热情接待(1985年的“阿城热”)与1990年出版的商业出版社对其翻译作品的沉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9]
无可否认,阿城(如鲁迅)是一位很难翻译的作家,在英文译文印刷时,“中国热”已经冷却下来,但似乎还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另一个例子是诗人多多在英文翻译中的第一次收集,[10]10也由商业出版社出版;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几周,当时就广为宣传,但在十二个月内仍然存在。
作家,观众和权威声音
比较作者与上述受众,我们发现作者与第一,第二和第三类受众之间的惊人通信:他们都是自觉社会群体的成员或潜在成员,即“知识分子”。选择探索情感或小说态度的中国作家倾向于采用智力主角/叙述者,并以尊重对待他/她的倾向受到这些观众的同情。
这种反常现象是,第四种观众(中国以外的非中国人)为了享乐而缺乏与中国作家的这种共同点。这种第四种读者可能被归类为知识分子(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但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角色有着截然不同的概念,而对文学中知识分子的描绘则有着非常不同的期望。第四听众对非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偏好通常被讽刺或厌恶地描绘(如图书销售所表明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作家所忽视。
下面讨论的作品不一定代表中国现代文学的整个身体。它们是主观写作的第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内心心理状态与外部社会变化有关),其次,它们被作者直接或间接地识别为自画像。这里列入的第三个标准是它们受到了第二和第三位观众的关注:它们构成了普遍接受的标准的一部分。所有的例子都来自小说(全长小说,小说和短篇小说),它提供了最广泛的作家声音实验范围。选择在某些方面是随机的,当然不是穷尽的:可以选择其他有用的例子。我的目的是说明“自我”(男性或女性)的概念化是如何提出一个群体的抽象的,通常理想化的肖像,而不是探索个性化的身份。
II
王安忆(生于1954年)来自一位作家家庭,在知识分子被公开修复的时代达到成熟。当她写下她不认同社交的角色时,王安忆描绘了由于社会的狭隘和腐败而残害的人们的现实肖像。然而,写作知识分子,尤其是女性知识分子时,她创造了非常理想化的角色,这些角色似乎是自我肖像的简单伪装。从构成她着名的“浪漫”三部曲的第二卷和最后一卷的两个故事:《荒山之恋》(荒山上的浪漫)[11],《小城之恋》(在一个小镇里的浪漫)[12]11和《锦绣谷之恋》(锦绣谷的浪漫)[13]
《小城之恋》
前几页介绍了小城镇浪漫主角的内容如下:
省演艺学院舞蹈系的一名老师与剧团进行了一天的课,并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内发现他们通过不正确的训练摧毁了他们的体质。他们没有肌肉,只有肉体,既没有灵活性,也没有力量。老师甚至把她(主角,名字从未给)放在工作室中间,转过身来,指出每个人的腿部,臀部和肩部通常都是变形的。问题确实很严重;她腿粗壮,手臂粗壮,腰部粗壮,臀部非常宽阔。她的乳房是正常大小的两倍,像小山一样突起,几乎不像十四岁。整个剧团在省学校舞蹈老师的催促下,仔细检查了她的身体,这让她感觉很糟糕。当然,她很惭愧,为了克服这种羞耻感,她穿上骄傲和鄙视的样子,高高举起头,把胸膛伸出来,然后看着眼角的其他人,就好像他们在她的下面一样。[14]
由于四人帮的文化政策,由于不适当的训练而造成的一名年轻女孩身体扭曲的描述,以及在新政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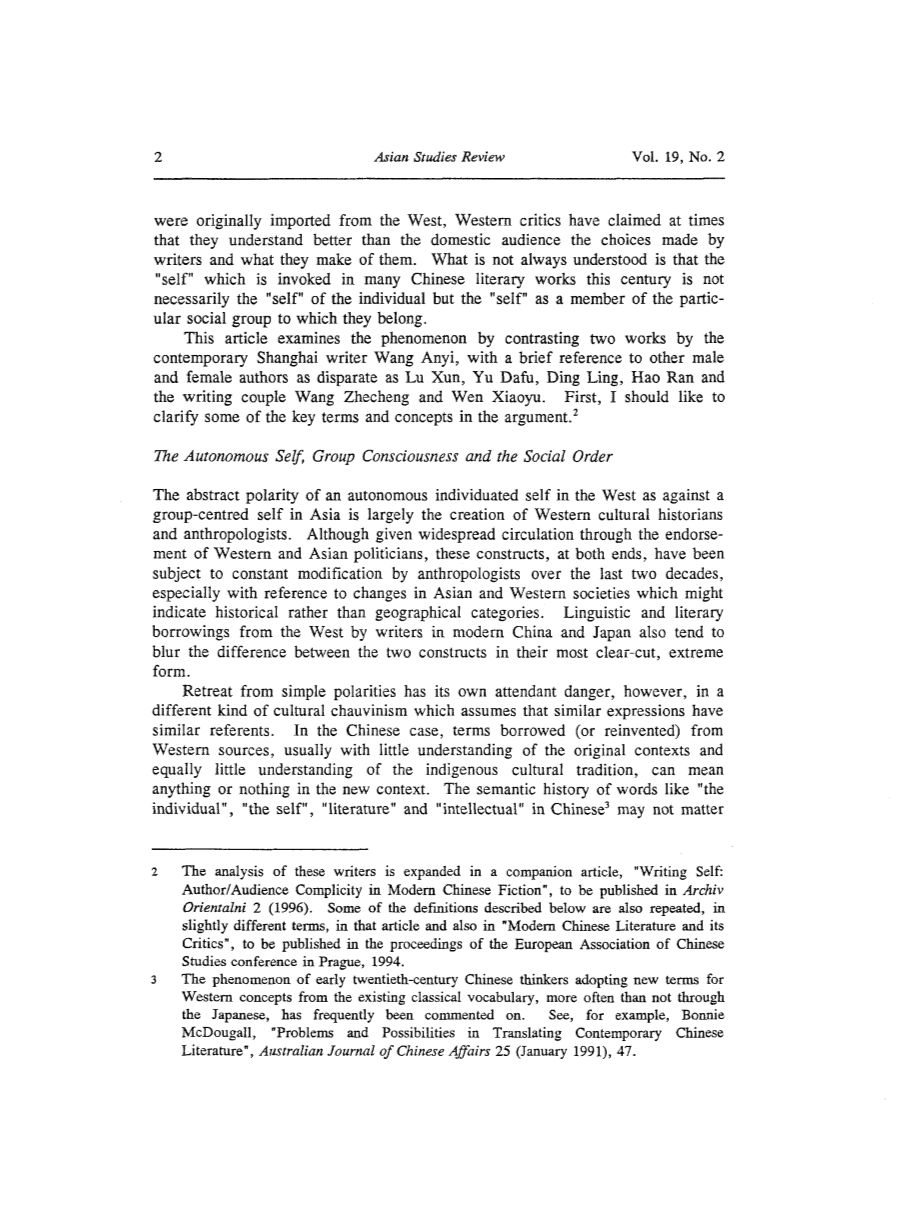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24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279240],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