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译者翻译职责的视角看《三体》的翻译外文翻译资料
2022-12-12 17:05: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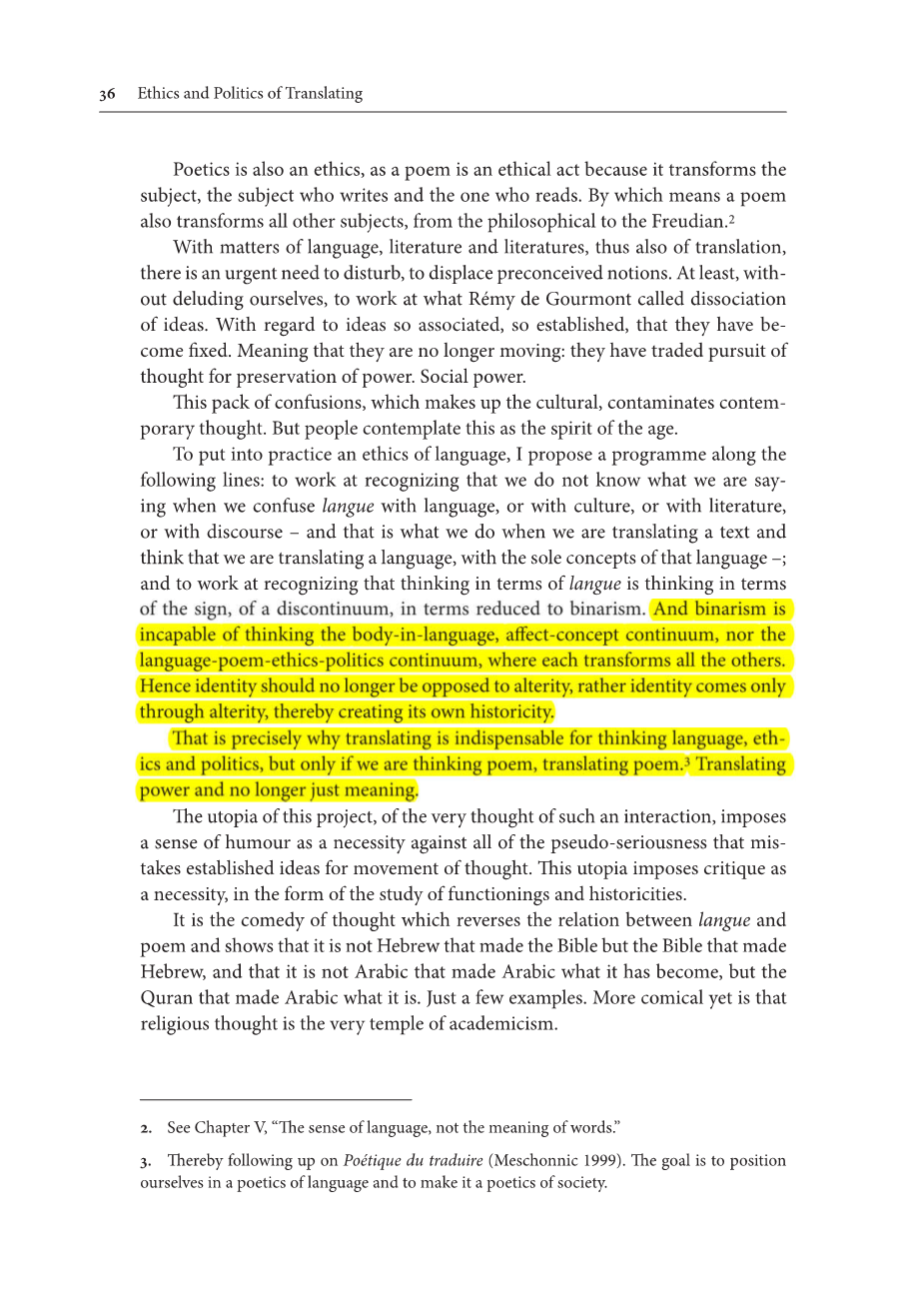
英语原文共 6 页,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第一章 翻译的伦理
翻译的伦理暗含了所有语言的伦理。而语言的伦理则暗示了语言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就霍克海默的方法而言是一种批判性理论,和组成现有不同种类的学术理由和原则的局部理论相反:语言学家的语言(包括所有技术性区别,当然这些都是必要而真实的),文学理论家的文学,哲学家的哲学,以及根据学术原则、伦理专家的伦理、各领域专家的政治哲学等的分界线,各个专业的伦理都各不相同。
当考虑到除去诗学之外的语言,而不是考虑诗学中的伦理和诗学中的政治,对于社会的诗学来说,这仅仅就只是学术性的了。它保持着学术上的双重性:它的符号和整个变格,它的文字和精神,它的同一性和他异性,都被神性政治所缓解了。
而这些想法困住了翻译概念上的忠诚和准确。忠诚于什么?语言吗?那是对源语还是目标语忠诚呢?但是语言和语言文字并不是同一个概念。我们必须有意识对这两个易混淆的概念加以区分。
如果不从伦理方面来考虑语言文字的话,一个典型的混淆概念就会出现,尤其是谈到诗歌的伦理时。例如,在我看来,列维纳斯的伦理和海德格尔的就十分相通,这种语言、诗歌的广义主流性把整个翻译置入理解中,这种观点至今仍被许多学者所推崇,保罗·利科就是其中一位。
我并非把伦理定位为一种社会责任,而是作为一种主体,在自己进行活动的过程中能不断发展自身,但是这主体的活动是在于另一个主体在完善自身的过程中所进行的活动。这样看来,作为语言的存在,这个主体是伦理和诗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也是这种一致性的某种延伸,即语言的伦理同语言的一切存在、人民的人性相关,也正因如此,伦理的也是政治的。
诗学也是一种伦理,诗歌是一种伦理行为,因为它转变了写和读的主体,即作者和读者。这也就意味着,诗歌同样转变了其他主体,从哲学的到佛洛伊德的。
就翻译的语言、文学和文学作品来说,有一项非常紧急的需要,即置换先前已有的一些概念,至少,不能欺骗我们自己,去做古尔蒙称之为概念分裂的事情。至于一些已经建立起来的紧密联系的概念,基本上就已经固定下来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几乎是不会改变了:它们是拿对思想的追求换取了权力的留存——社会性权力。
这一系列的混乱,组成了文化,同时也污染了当代的思想,但人们认为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
把语言的伦理放到实际中来看,我认为它是按照以下一程序来运作的:当分不清语言和语言文字、文化、文学或者对话时,努力去识别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翻译一篇文章时所做的事情,翻译一门语言时所需要思考的,我们应当对该门语言有确定唯一的概念。努力去识别和思考语言就是思考标识,思考间断统,明确地减少至二元对立。而二元对立就是没有能力思考身体在语言中、影响-概念间断统,以及语言-诗歌-伦理-政治间断统,而在这其中它们都能进行互相转换。因此,同一性不应该再置于他异性的对立面。相反,同一性正是从他异性中演化而来,也正由此创造了其历史真实性。
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翻译是独立于语言、伦理和政治的思考,除非我们是去思考和翻译诗歌。翻译性权力将不再只是一句空话。
这一项目,对于这种互动的深刻思考的乌托邦,将幽默感作为一种对抗所有伪君子式严肃性的必需品加注其中,所谓伪君子式严肃性将已建立的概念群错误得用作了思想运动的指向标。这种乌托邦将批判作为一种必需品,用功能性和历史真实性的研究对其加以包装。
这可以说是思考的一场闹剧,将语言和诗歌的联系完全扭转,好像在告诉我们不是犹太人写就了《圣经》,而是《圣经》创造了犹太人;好比不是阿拉伯人造就了阿拉伯语,而是《可兰经》成就了阿拉伯语。只需几个例子,足可说明可笑的宗教思想是形式主义的神殿。
当然,并不仅是如此,有无数的证人可以证明,包括一些名人。但某种程度上,几乎没有例子会被进一步证明是正当的。
所谓翻译伦理,我假定它是由一种语言的伦理在一种包含在内的语言理论发展而来,没有以任何方式竭力得假装,我们需要看到已经做出的努力。我在学习翻译中所可能得到的全部经验,给我带来了一些光明,那就是翻译伦理这个概念总体来说是绝对的。正如我在翻译中所学到的,翻译伦理的立足点在于习惯性的伦理。根据译者行为的总体准则,它关注译者的忠诚和自我消亡。但是翻译行为的准则,无论是如何基础和必要的,都无法得到满足。
- 翻译行为的准则得不到满足
如果诗学缺失,那么翻译行为的准则将永远得不到满足。这就是当前的现状,几乎是司空见惯的。这也是安东尼·皮姆对他作品的定位,冠以一个充满希望却欺骗性的标题:“翻译的伦理”。
这里的伦理既不是针对翻译的行为也不是翻译的内容,而是针对译者。我们也许会认为这三者不就是同一个概念吗?实际上并不是。
安东尼·皮姆的著作在一开始就定位了在源语/目标语间如何翻译。对于源语文本,更看重作品本身;而对于目标语文本,则将重点放在“沟通”这一目的上。这些都是非常传统的观点。二元对立反对“空谈理论家”和专业译者。因此,二元的伦理也即,缺乏实践的伦理,缺乏伦理的实践。
安东尼·皮姆认为他正在远离这种二元对立,通过以“应当翻译”取代“如何翻译”的提问方式。事实上,是“为什么翻译”和“为谁翻译”取代了“如何翻译”。并且他提出了一种“内容伦理”的概念——译者应当和不应当的翻译——这种伦理是抽象的,并且漠视了内容。但这种方式不再适合当今的翻译。皮姆正在找寻“跨文化原则”和“以译者为中心的伦理而非评判翻译本身的伦理”之间的折衷地带。
这使得他第一个投向了施莱尔马赫的解释学,接下来就是传统的二元论、经典学,以及西塞罗《作为演说家》中的“二者择一”论、圣哲杰罗姆的意义和文字的对决。而尼达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对决则并没有任何新内容。这似乎是当前非常客观并且也是传统的翻译问题:读者要不就“呆在家里”(翻译过于异化),要不就“云游海外”(翻译过于归化)。
安东尼·皮姆尝试着通过将问题转向“译者的身份”来打破施莱尔马赫的这种二元对立,而奇怪的是这反而终结了向“外交豁免”问题的转移。在关于伦理这方面的考虑,他在“整体愉悦”和“个体权力”这两个陈词滥调中迷失了方向。这完全是因为一个“纳粹式翻译者”,一个美国谈判专家被告上法庭,并且翻译萨尔曼·路西迪《撒旦诗篇》的一些翻译家被一些伊斯兰教主义者给谋杀了。安东尼·皮姆由此得出结论,译者职责包含着一种“跨文化伦理”,并且他认为这种职责是“翻译伦理的基础”、一种“职业化的伦理”、规范化的却又不同于仅仅遵循着某些“处方”的伦理。
然后他又利用特有的哲学主题,因为“伦理是由意识和理智发展而来的”。因此,诗学并没有被真正地回避掉,只是一开始就没有将其考虑进去。
但是他所利用的所有这些概念中,包括“翻译竞争”,都是表达了“某些人对翻译很在行,其他人却不行”。那么翻译的标准到底在哪里?皮姆把翻译作为一项专业性实践活动,使其与“一种不要求伦理的非人格性程度(超越明确规则)”相联系,这就消除了关于这项议题的任何思考。
并且把他引入了诸如“译者被算作一种职业是因为他提供翻译这项服务,还是他提供了翻译成果这种商品?”的问题。但这些明显都是不可分割的,因此这问题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既然要想进行翻译行为,译者“必须生产出翻译这项商品”)。他又再发现了一个显然的事实:翻译“即不算引用”,“又不算注释”。他自行回避了“忠诚”这个概念,但同时用“职责”取代了“忠诚”。
皮姆想要一种翻译伦理,而所有他最后得到的是社会道德。他唯一提及到诗学的地方是“平庸的诗学”在“翻译的潜在应用”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四项指标:物质的、最终的、正式的、有效的——正如译者所呈现的。根据亚里士多德作品的译者特里克所说,一个人所发现的,正是“事实和形式的关联”。这是二元对立的标志,与诗学无关。
剩余内容已隐藏,支付完成后下载完整资料
资料编号:[30812],资料为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可免费转换为Word




